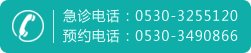做了三十年医生的父亲,尝试从他的经历和视野中寻求一个解决医患矛盾的答案,最后发现只有做鸵鸟才能自我保护。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他希望建立起更健全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也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今年是父亲做医生的第三十年
三十年来,医患矛盾不断加剧,在我们这个西北地区农业人口占主导的小县城尤甚。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每年都要面对无数病人和家属的误解、谩骂,甚至还有病人家属扬言要「收拾」父亲;偶尔也会发生实实在在的肢体冲突……
有时候,父亲会抱怨,这个职业让他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常常睡不好觉,高血压似乎也越来越严重了。
但他又离不开这个职业。他总是会津津乐道于哪个病人又被抢救过来了,医院又帮哪个家庭困难的患者垫了医药费;甚至也会高屋建瓴地分析基层医疗的现状,以及如何改进医患关系。
每到年末,当这一年平安度过、医院里没有发生大的医患纠纷时,父亲总会深深舒一口气。
在他的字典里,「健康」和「平安」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管是对于家人,还是病人。
迟到的年夜饭
和往年一样,今年除夕,父亲仍旧没有在家里吃年夜饭。
这三十年,父亲从一名普通的基层医生做到了管理层。唯一不变的是,每年的年夜饭,他都会在医院吃——做基层医生时,他在一线值班;做了管理层,他要慰问除夕夜在一线值班的医护人员。
久而久之,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挪到了正月初一这天。
而我和母亲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就像我们早已习惯了父亲随时可能会被深夜的一通电话叫去医院一样。
轮到父亲值班的晚上,我总是听到父亲的值班手机不断响起。后来做了记者之后才发现,当年父亲的值班手机简直就是社会新闻热线的翻版——总是有光怪陆离的伤情病情发生,比如,有人在爬山途中被闪电击中猝死。
我的童年记忆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我至今记得的场景是:在门诊部里,父亲穿着宽松的白大褂、拿着听诊器在病人的胸前摸索。而在我关于日常生活的场景里,父亲的面目始终是模糊的。
父母的工作总是很忙。年幼时,我一度痛恨他们的「冷漠」。三四岁时,我生了一场病,在父亲工作的医院打了一个礼拜的点滴。整整一个礼拜,父母几乎都没有时间照顾我——我被拜托给了父亲的医生同事们。
对于这件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我第一次为父亲的职业感到骄傲,才渐渐释怀。
那时候,我们家还住在老家的巷子里,周围都是熟悉的街坊邻居。他们有个头疼脑热,总会请父亲帮他们开张药方。而父亲也是乐意为之。
为了感谢父亲,邻居们做了好吃的都会送些给我,有土特产也会捎一份给我家。就连和父亲一起走在巷子里,我都能感觉到邻居们看父亲的眼神带有一丝丝的敬仰。
那时候,在父亲工作的医院,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也总是挂着一面面锦旗,上面出现最多的字眼是「妙手回春」。
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职业还有那么一点点神圣。
但很快我又意识到这个职业的危险。
一次外出回家,我听到父母神色紧张地感慨:「幸亏她不在家。」在我百般追问下,父亲才跟我说起,在我外出的时候,我们小县城里一个有名的瘾君子跑到家里来,希望父亲给他开几剂杜冷丁(一种临床应用的合成镇痛药,作用和机理与吗啡相似)。父亲以没有权限开麻醉药拒绝了。瘾君子周旋了一阵,看确实没什么希望便走了。此后,父亲一直心有余悸,生怕他再次造访。
好在,没有第二次。
流失的信任感
从十年前起,父亲就不做一线医生转做行政了。但他似乎更忙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看起来是变得更闲了,但实际上心却更累了。
这个时候,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父亲给我讲过一个关于误解的小故事。
一次,一个在乡镇的病人家属打 120 叫救护车。碰巧,医院的四辆救护车全都外出了。病人家属只好自己找车把病人送到了县城,但到医院门口时,病人已经快不行了。而此时,这位家属正好看到医院院子里赫然停着一辆救护车。
质疑随之而来。
「明明有车为什么不派?」「如果派了,病情就不会被耽搁。」病人家属的怒火一触即发,之后,四十多位病人家属堵住医院大门要求索赔。直到派出所介入,给病人家属看了医院当天的视频监控,疑虑才被打消。
真相是,在这位病人家属的车到医院门口的前几秒,他看到的那辆 120 救护车才刚刚回到医院。
「就是一种不信任的感觉。」父亲事后总结。

图:除夕这天的医院
而对父亲的外科同事们来说,这种「不信任」和「被怀疑」的感觉更加明显和频繁。
在手术前的医患谈话中,越来越多的病人家属会用手机录音、拍照。这让父亲和他的很多同事们觉得心寒,「就好像是已经做好了一定会发生事故的准备,准备和医院打官司,而医生有绝对的责任。」
发生医患纠纷后,即使医院没有过失,病人家属一闹,迫于上级压力,医院也只能忍气吞声——赔偿。
时间久了,赔得多了,医院也开始学会「鸵鸟式」的自我保护——为了避免可能的纠纷,碰到比较难缠的病人,直接让他们转诊。
父亲有些无奈,明明是可以在县城医院治好的病,非要去三甲医院。病人有了更多的额外支出,也给上级医院的医疗资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但如果不让转诊,如果出现医疗事故,又将是漫长的医患拉锯战。
有时候,发生医疗纠纷后,父亲会接到病人家属的电话。还没等父亲开口,电话那头用近乎狂躁的语气大骂:「你们这些无良医生!」「你小心点!」挂了电话,父亲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苦笑一声。
「都会好起来」
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感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父亲不知道,但他一直想知道。
在过去一年里,父亲所在医院的鸵鸟原则,让医患纠纷数量下降了一大半。但弊端也很明显,我们这个小县城二级医院的转诊率达到了 15%——超过了上级规定比例的 5 个百点。
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好事——病人越来越少,县级医院运营状况堪忧。
父亲常常会跟他的一线同事们说,对病人多一些理解,留住更多的病人。但他更真实的想法是,要是有更有效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医生和病人都没这么艰难了。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位高龄博士产妇在医院怀孕生子猝死的新闻给父亲。
父亲自然觉得医院是弱势群体。「产妇死因是主动脉夹层破裂,和医院有什么关系呢?还居然以单位的名义出来质疑医院。」父亲有些义愤填膺,「这时候卫计委就应该出来声援医院。」
「声援有用吗?」我问。
「当然有用了,要给我们医护人员信心和尊严。」父亲有些执拗地说。
在不被理解的时刻,只有医生才能理解医生。这是一种同行间的守望吧,我想。
现在,我们家已经搬离了老家的那条巷子,住进了单元房。熟悉的邻居们已经变成了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偶尔见面只是点头寒暄,不再有街坊邻居找父亲来开药方了,更不会有邻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拿手厨艺和土特产了。
父亲时常会怀念十多年前在一线做医生的日子——那时候,工作内容单纯,医患关系也没那么复杂。
前一两年,父亲总会在朋友圈里分享许多关于医患关系的文章。这一年,少了很多。他明显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如从前——睡眠不好、记忆力衰退、血压还在升高。
他决定不再想那么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有时下班后,父亲找几个朋友爬爬山,路上聊聊天。站在山顶上俯瞰小城全景、凉风掠过脸上的汗珠,那个时刻,所有的烦恼都忘光了。
在北京工作后,我明显地感觉到父母的孤独。和母亲经常电话叮嘱天气变化的唠叨相比,父亲对我的思念更加隐蔽——他会时不时在微信上和我分享工作的细节、自拍照、以及爬山时遇到的风景。他乐此不疲,不管我会不会回复。
这次回家,我在自己房间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地图册,唯独北京地图这一页被翻得很旧。
我几乎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想念我的时候,父母坐在我的房间里,翻开这本地图册,触摸我工作的东城区,再寻找我住的朝阳区……
我想,过年这几天,我应该多陪他们聊聊天。